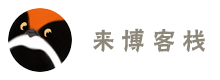早晨五点半就上了车,向炉霍进发。
和甘孜州别的地方比起来,炉霍是一个建筑相当新的县城。1973年2月6日,炉霍发生7.6级地震(当时测定为7.9级)。 现在看到的建筑多是震后重建的,所以看起来十分光鲜。
我们把大个儿的行李放在炉霍卡萨大酒店,中午出发前往玲珑寺。 玲珑寺在炉霍南面二十多公里处的一条叫做易日沟的山谷里。 车到易日沟并没花多久,可从易日沟入口处到玲珑寺的路却很差,车走了一个多小时。 许多地方都需要我们下车,搬运木石,铺路垫桥。 虽然路很差,四面却是山壑幽深,峰林秀美,几疑世外桃源。 一条小溪汩汩地从山谷深处流出来,咚咚的水声时常相伴左右。
玲珑寺的住持是秋吉尼玛仁波切。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在忙着处理牧民之间的纠纷,我们在客堂等了片刻才见到。 仁波切身材很魁梧,面庞黝黑,目光明亮锐利。他用厚实的大手为我们逐一加持。 当加持到别人时,我瞧了一眼,只见他双目圆睁,示现愤怒明王相,但当他收敛眼光时,却是宁静慈和。

玲珑寺的连排独栋僧舍
我发现藏僧和汉僧,或在藏居士和汉居士之间,有这么个不同之处:精进的藏僧(或居士)和我们交谈,听起来全是生活琐事;而精进的汉僧(或居士)说起话来,却是佛法不绝于耳。
见过仁波切,我们去管家巴登曲扎的住处小坐了一会儿。玲珑寺的僧舍是度假村级的,每座僧舍都是个独立的小楼,使用面积起码一百平方米,还有卫生间。僧舍的布局也很有章法,依山傍水连排别墅。
我们问巴登曲扎,这里的像你这样的一座房子要多少钱呢?他说,一万块就可以盖一座,只要提前一年预订即可。在这一年内,工匠们要选木材,把木材在水里浸泡,再拿到太阳下晒,如此反复多次,保证房子盖好之后不会出裂纹。
听到这些,再想想北京地产商的谎话连篇的宣传和高居不下的房价,大家感慨良久。

逢人就顶的老山羊
玲珑寺有一头白色的老山羊,据说它整日价在寺旁逡巡,逢陌生人就顶。事实也确实如此,它一见我们,就大踏步走了过来,随机挑选一个欺生对象,靠近了,先用牙撕扯衣服或者背包带,随后就是一歪脑袋,一双明晃晃的角咣当顶了过来。最厉害的一次,它甚至前蹄腾空,人立起来,恶狠狠地对着高峻猛扑。我们到巴登曲扎家的时候,它跟到了门口就不往里进了。我们以为把它甩掉了,谁知道从巴登曲扎家出来的时候,发现它就在路对面的墙根下趴着。也就是说,它一直在那里候着我们。我们刚跨出门槛,它就抖抖身子站了起来,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势。
玲珑寺正在建一座坛城,巴登曲扎带我们去看。坛城的中央大殿里供奉的是莲华生大师,四围佛像尚未安放。 坛城顶的密意坛城的地面上放着四十二尊佛像,还没有打开包装。

玲珑寺坛城上工匠调色的习作
在坛城的一面木墙上,我们看到了一些随意勾勒却生气盎然的图案。巴登曲扎介绍,这些是画装饰图案和壁画的工匠们调好颜色之后,试色时画的。
从坛城出来,发现我们放在外面车上的饼都被老山羊啃了,可这些饼是秋吉尼玛仁波切刚刚赐给我们的啊!最可恶的是,这老山羊还照着中间啃,啃出一个圈来,我们都没办法掰掉它啃过的地方。高峻抓着它的角和它打架,它也不示弱,吭哧吭哧地埋着头又踢又打。
晚上回到炉霍,明天去道孚大神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