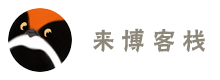寻找毛子强(二)
- 2013年04月4日
北京的春天是灰黄色的。浩浩荡荡的风裹挟着一天沙土,在虚空中轰隆轰隆地运行。有的土不想再去天津,就提前下到地面来了。我走在满是土腥味的风里面,身后拉着两道黄烟,悻悻地想,同一个黄色大锅盖下,还罩着毛子强先生,他有一辆车可以挡土,我却在这里一边喝风,一边还得替他接电话。
找到毛子强的那天,我要把手机漂亮地甩到他桌上,狞笑道:车,老子开走,轮到你接电话了!
有时我又咬着手指头想,干脆,下次再有保险推销电话,我就替毛子强续上五十年的保险算了,谁家的保险都要,反正走毛子强的帐。
刚起这个念头没多久,车管所给我发了条短信,说,毛子强先生,你的交强险已到期,年检也得做了。
这意思是说,有那么一晚,我拖着两腿回到家里。刚刚拽开门,就嗅到浓重的生人气息,正自惊疑,几个黑影从房子四角悄没声地掩了过来,一声唿哨,俺被按倒在地,几束刺眼的电筒光柱齐刷刷打到脸上,黑影甲喝道:毛子强!你闯灯肇事,撞死那么多人,终于抓到你了!黑影乙对着步话机喊:洞洞幺,洞洞幺,目标定位成功!目标归案!
还没踢飞毛子强的门板,毛子强先把我生擒。这可不妙,我得抓紧了。
我到网上去搜毛子强,头几页的结果是:
鬼子强还是毛子强?
德国人再狠也比老毛子强。
五毛被毛子强奸,还高兴得要死……
算了,老子认栽。一分钱一分货,免费的路子不靠谱。
多年前,和同事们包车去京郊。吃饭时,包车司机凑上桌来,摸出几份保险传单,恳请我们照顾一下,留个联系方式。俺犹豫片刻,把手机号后几位分别加一减一,名字也填了个假的。后来问同事,他们也各有高招。司机大叔的怨念,也许幻化出了毛子强。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啊。
对那个终极问题“你不是毛子强那你是谁?”我的确没有把握回答,从小到大,见到的人都叫我田深,然后我就信了,还对初见的别人这么介绍自己。可现在大家叫我毛子强,我却不肯信,还想在北京城的某个会所里把毛子强揪出来,证明给大家看。
这一定是因为小孩子容易哄,我一身冷汗地想,幸好,从小大家没把我称作一条狗。
我又一身冷汗地想,万一我就是一条狗,而只是被大家定义成了人呢?想到这些,我两手不禁动了起来,试图再确认一下自己既没有尖牙也没有尾巴。
没用的,一个声音淡淡地笑道,你眼里的、耳朵里的、心里的世界都是你自己的,如果你早已认定自己是人,那么你当然摸不到那条狗尾巴。你说的狗,也不是大家说的样子。
有时我又想,可能我真的就是毛子强,或者毛子强就是我。道家有门方法叫夺舍,舍者,房子也。房子者,身体也。也许毛子强夺了我的舍,也许是我夺了他的舍,可不管怎样,都没法退货了。
站在地铁里,我盯着对面的小朋友想,万一我把持不住,灵魂在躯壳里这么一挣,就会霎时间透过他的视线,回望到曾经的我自己,只见他目光瞬间焕散,面色松驰,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车厢里四下惊叫,而我,低头凝望这被我住得敝败废旧的躯体,看他的瞳孔慢慢放大,手脚在脊髓的控制下无节律地抽动。他吐出最后一口浊气,是两秒钟前由我吸进去的。裤裆湿了一片,是他失禁的尿液。在他的头骨里面,大脑开始液化。他只是一坨肉而已了,我平静地转身,挤过身后慌乱攘动的人群。屏蔽门开了,我面带得色地走了出去。
妈的,夺舍之前,我应该先摸清毛子强或者我自己的家底的。那辆倒霉的奥迪车,也不知在哪个该死的停车场慢慢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