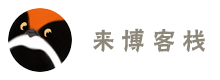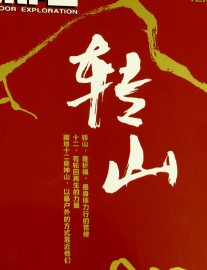珠穆朗玛,2006年7月
最高跑到过珠峰大本营(5220米),却还从未体验过高原反应。最近和新识的高原旅行者@下导交流关于阿里的路况,得知人对高原反应的感受是这样的。
下导的旅伴葫芦娃叙述(原文在此):
我突然觉得饿了,不仅把自己的面吃了,还把条七吃剩的吃不下的面也吃了,我觉得我身体反应这么大也可能是没吃饱造成的,饭总看我吃了条七的面,也把条七剩下的几棵青菜挑出来吃了,他也是个饿死鬼。吃完我们就回房休息了,因为明天一早还要赶路。我把自己的背包背上二楼,头疼加脚软,就不准备在天明之前下楼了。
我准备了四罐氧气,抱着睡,小立准备了两罐,小立还去弄了一个氧气包回来,自己先吸了一会,说洗完可以到老板那里去充,充满之后再给我吸。我自己先吸了一瓶,过了会饭总来敲门说帮我们一起把氧气包充满,之后我就抱着氧气包睡了。我和小立、条七睡一间。条七不一会就鼾声震天了,无高反人群真幸福。
我太累了,其实也马上睡着了,但不知过了多久,又被憋醒了,总感觉胸口闷,头疼欲裂,用手指在头上的各个穴位死命的按来按去,想撞墙,想回家……四肢慢慢从内而外的发冷,我吓得不行,赶紧又吸氧,折腾了几下我就把我的氧气配额用光了。
半梦半醒间,我觉得应该天快亮了吧,找块表一看,擦,才凌晨两点,我了个去!这里是八点才天亮啊。我一下子慌了,我们这几瓶氧气已经是最后几瓶了,昨天在定日买了一箱都被我们在珠峰吸完了。一慌起来就更加感觉头疼,人在绝境中只有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就会拼老命的抓在手里。店老板睡前跟我说,氧气包吸完可以叫醒他加氧气。我套上我的航海衣就夺门而出,先是一口气窜到餐厅找老板,一个人也没,出来后找到一个写着值班室的房间,门虚掩着,我跑到门口已经快虚脱了,大口喘了几下,敲敲门,灯马上亮了,28岁老板的黑脸膛在我看来就是救命的观世音。他很快披了两件衣服出来,身后我隐隐听到床上有女人的抱怨声。老板把我带到氧气房,这里有一大钢瓶氧气,那是我的命。还有一张无比脏的木头床,我看到有几条蜈蚣爬过……。老板把我的氧气包充满,我勉强半个屁股坐在那张很脏的木头床上大口吸氧,老板等我吸完又给我充满,说:等这包吸完应该差不多了,我先回去了,你吸完也赶紧回去睡吧。我从来没对一个男人那么不舍,我说:等会,那你……慢走啊,谢谢啊。
老板走了,我慢慢慢慢的把氧气吸完,感觉舒服了些,回房继续睡。又睡了一会,又开始四肢发冷了,我实在不好意思去麻烦老板和他姘妇,就死命挺着。
再过一会,竟然四肢开始不自觉的发抖和抽搐了,我想那时我就像一条快要渴死的鱼,临渴死前神经开始痉挛抽搐,我突然觉得自己可能连走下二楼去找老板的力气都没了。我开始叫小立,我说小立我感觉不太好,你还有没有氧气……他终于被我叫醒了,这个时候他也只有一瓶氧气了,他还是犹豫了一下,然后把氧气瓶扔给了我,我插上管子猛吸,几下就吸光了,浑身略有了点力气,还是要去向老板求助。
我突然又觉得自己很干渴,嘴唇上像扎满了针一样疼,就爬起来,把茶杯倒上水,喝干,再倒满,再喝干。这样几个简单动作,我感觉已经耗尽了小立刚让我吸掉的那瓶氧气。我几乎连滚带爬的下了楼,滚到值班室的时候,疼得已经直不起腰也抬不起头,只看到门仍然虚掩着,我撞开门就趴到门槛上了,我说,老板,快,我又不行了。
老板吓得也不轻,赶紧起床说,你先去氧气房,我马上到。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窜到氧气房,身子缩成一团。老板只穿了条秋裤跑过来把我的氧气包加满,我抢过来猛吸猛吸,几口就吸光了,老板又给我加满,我几口又吸光了,老板再加满……第二天老板为了我吸氧收费50元,他说本来他这里吸氧不收费,但是我实在吸得太多——他从没见过这样猛烈吸氧的人,也吓坏了……在吸完第三包的时候我感觉缓过来很多,身子软绵绵的,管它什么蜈蚣蟑螂还是瓢虫的,躺在了那张无比脏的床上了。
吸第四包的时候,老板冻得瑟瑟发抖,说他得回去了,现在是六点,还有差不多俩小时天亮,让我先挺住,天亮他起床再给我吸氧。我又一次对他恋恋不舍,我说,这氧气瓶我能自己充氧气不,28岁藏民老板大大的狡猾,说有危险,不能自用,就回去见他姘妇去了。我躺着吸完一包氧气,想了想,跑到氧气瓶旁边一看,那跟自来水龙头一样,把阀门扭开,对着氧气包的口就会有氧气喷进去。我又自己吸了也不知道几包,恢复了正常,回到房间去睡。
天终于亮了,我又一次奔去氧气房,老板已经起床了,姘妇们也起床了,兄弟们还在睡觉,我又开始吸氧,两个藏族女同胞看我实在可怜,不知哪弄了条棉被过来盖在我和蜈蚣身上,我很感激,才意识到真的很冷啊很冷啊。
下导本人叙述(原文在此):
5200的海拔在晚上绝对是一种折磨,我几乎完全没有食欲。亮亮吃了很多,结果血液集中在胃部,除了加剧高反之外也没能顺利消化食物,第二天就都吐完了。小立贱七和葫芦娃都凑合吃了点。只有饭总,总是能吃下很多饭,饭总。
每人吸完一罐氧气,又将气瓶分发到每个人手里,大家就在各自的床铺上睡下了。睡不着的人或发微博短信,或看手机里储存的A片毛片。
帐篷里点着的炉子虽然升高了帐篷内的温度,却消耗了原本就稀薄的氧气。我习惯性的采用坐姿入睡,这样可以减少一点缺氧带来的难以忍受的头痛欲裂,至少这种方法对我有效。但无论怎样,每每睡着片刻,就会被落水窒息般的感觉弄醒。
在这个晚上,葫芦娃的噩梦降临。从这一晚开始,在通向缺氧的高速公路上,葫芦娃就两脚都是油门了。
半睡半醒间,我听到葫芦娃不停的起来,喝水,吸氧,躺下,起来,喝水,吸氧,躺下,起来,喝水,嘘嘘,吸氧,躺下。
我知道他肯定很难受。不过其实我不比他舒服多少。几乎每十几分钟就会醒来,头疼得像要从里面爆裂一样。然后,宁可忍受零下的低温的风,我也要跑到帐篷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再点上一根烟,缓解一下头疼的感觉。
到后半夜,我觉得实在不能再忍受帐篷里的低氧环境了。我爬到了停在外面的陆巡上,摸出羽绒睡袋从脚裹到头,将窗户摇下一点点,顿时觉得神清气爽了不少~
但头还是疼啊疼,疼到恨不得大声哭出来。还有就是温度太低,浑身上下都打战,基础体温低导致虽然是羽绒睡袋但温度上升得很慢。担心油不够,也不敢发动取暖。
迷迷糊糊中好像看到葫芦娃又出來嘘嘘,从他的步伐中可以看出,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在草地上欢快奔跑或是在路标上摆出造型的无邪少年了。
这一刻,老纸自身难保,也就顾不得向他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了。
传说,在珠峰登顶的那一段,登山队员们基本上不可能向需要帮助的队友伸出援手,只能看着他们无助的死去,在这个大本营之夜,我算是彻底理解他们了。
…………
记得07年第一次从青藏线进来的时候,在安多,第一个在4000米以上的夜晚,老纸也是(和葫芦娃)一模一样的感觉,就是-“胸口闷,头疼欲裂,用手指在头上的各个穴位死命的按来按去,想撞墙,想回家……四肢慢慢从内而外的发冷”。
期间醒来无数次,在前所未有的头疼和犯困中挣扎,睡着一会,醒来一下,头疼很久。
那时要是有马上可以回家的航班,老纸会毫不犹豫的跳上去,回家。
但因为老纸那会差不多是孤身一人,手头也只有一包氧气,既无人可以求助,也不好意思去叫醒服务员,所以只好硬挺。发现坐姿的时候头疼略有缓解,于是穿戴整齐坐起来等待天亮。
实在困到不行,老纸就把枕头放在窗台上以上课睡觉的姿势小睡一会,实在疼到崩溃边缘了,就独自放声嚎哭一会,反正一个人也没啥丢脸不丢脸的~

昆仑山玉珠峰,2006年速写
下导说,第一次上高原如果出现反应,以后再来,就还会有。当然本次旅行中,会逐渐适应。
我的经历,虽然自己未能体会高反,却永久治愈过一位朋友的。2005年5月,大家都是第一次上高原,躺在稻城的汽车宾馆里,外头灯箱透过窗帘,晃得屋子里贼亮。我看他躺在床上,呼吸粗重,辗转反侧,时不时哼哼一声。问他,说头疼。无法体会他的疼法,觉得除了缺氧外,应该是体内气压高,血管里可能有氮气泡,排不出去。我想起自己平时是腹式呼吸,既然我不疼,也许可以帮到他。
我让他平躺,两手摊开,手心向上……唔唔……对……就是解剖标准姿势……浑身放松,尝试轻缓悠长的呼吸。吸气时,不用胸脯,而是从小腹开始,自下而上带动肚皮,缓缓鼓起,带动体内横膈膜下降。吸气和呼气的转折要轻缓,要连自己都听不到。吸气时,想着手心和脚心同时进气。呼气时,想着全身每个毛孔都在悄悄地散掉。
然后……我陪练五分钟不到,就可耻地先自己睡着了……
天亮,他向我汇报说,方法太灵了,很快就不疼了,舒服地睡着了,然后就回复胸式呼吸了,然后就疼醒了,然后就再腹式,再睡着,周而复始……
他后来再上高原,就再也没有高原反应了,包括珠穆朗玛脚下,是我最得意的搭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