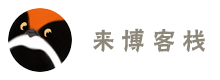辨识佛像——弥勒菩萨
- 2012年08月19日
弥勒菩萨?很多读者会大跌眼镜地说:弥勒减肥了?励志啊!
其实弥勒菩萨本来不胖的,只是因为五代后梁时,有一位笑眯眯的布袋和尚被认作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弥勒菩萨的报身一直是英俊健美的。
有时我们称弥勒佛,有时称弥勒菩萨,是因为参照点不同。说他是佛,是因为他被授记为未来佛,说他是菩萨,是因为他现在尚在兜率天代替释迦牟尼佛说法,还未下世成佛,所以称菩萨。
虽然指的是同一位,但造佛像和菩萨像有不同的法度。所以弥勒菩萨(佛)的形象比较复杂繁多些。识别弥勒菩萨(佛)的造像,要留意这样几个特征。
善跏趺坐:也称为“垂足坐”,就是坐在椅子上两脚自然下垂着地的姿势,像右图那样,这是随时准备下生成佛的姿势。释迦佛从兜率天起身,说:“我要成佛去。”把说法的任务交给弥勒菩萨。起身前,他可能就是这个姿势。而现在这姿势是弥勒菩萨的,也隐含着他是未来佛的意思。弥勒佛则无此姿势,而是全跏趺坐,表示彼时他已圆满涅槃,不需要随时准备站起来了。
说法印:释迦牟尼佛已经涅槃,弥勒菩萨正在天道说法,所以弥勒菩萨手结说法印。弥勒佛的形象也是双手说法印。如果一尊佛像,简单到没有其他任何特征可供辨识(腿的坐姿、铭文、装藏经文、肩花、等等),却只剩双手说法印的姿势,你就可以毫无愧意地把他认作弥勒菩萨或弥勒佛。虽然文殊菩萨也常结说法印,但文殊菩萨毕竟还有很多可供选择的其他姿势,如右手举宝剑。弥勒菩萨除了说法印,可供选择的余地太少了。
肩花:弥勒菩萨的肩花是一只军持瓶和一只八辐金轮。军持瓶——想象一把普通的带盖茶壶,去掉柄,就是军持。这是灌顶时常用的礼器之一,弥勒菩萨在说法,用这个应该很频繁的。八辐金轮意思也是“说法”——很遗憾,有一个词,三个字,是很敏感的,我不敢说。大家知道它本来是正宗的佛教用语,后来被一个自称佛教的法门借走就是了——这三个字就是说法的意思,而八辐金轮与之相应。如果你在肩花上看到军持或金轮,任何一个,你都可以肯定地说这位是弥勒菩萨。
塔:弥勒菩萨如果头戴天冠,则正中间一叶上是一座佛塔。如果是弥勒佛,可能会托一座塔。我这里要辨析一下。汉地的药师佛也手托一座塔,是那种七级浮屠似的层层宝塔。藏传佛教造像里,弥勒佛手里的塔是覆钵式的,北京北海公园永安寺白塔那种。塔代表佛陀的法身,弥勒菩萨作为未来佛及释迦牟尼佛的代理授课老师,托塔或头顶有塔,都是由微妙寓意的。
顶上一幅图,现居国家博物馆。弥勒菩萨的布袋和尚化身那张图,是我家佛堂上自己供的。虽然造型俗气点,但这是门措上师赐予,所以不敢当等闲的“聚财纳福”看。第三幅是首都博物馆一尊垂足坐姿的弥勒菩萨,放大了看,说法印、善跏趺坐、军持瓶和八辐金轮、头顶的塔,一应俱全。第四幅,是未来佛的形象,只有说法印可供标识。不过这是三世佛里的一尊,有另外两尊在身旁陪着,这尊就太好认了。即使他是孤零零的一尊像,我们刚才说了,单看说法印,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他是弥勒佛。三世佛的概念,我在“药师佛”一章介绍过。第五幅,右边这尊,也在首都博物馆,是手中托塔的弥勒佛像,右手还打了半个说法印——要不说说法印重要呢。
下面这尊,是四川甘孜州道孚县灵雀寺的弥勒菩萨。殿内虽然暗,说法印虽被哈达遮挡,善跏趺坐姿、肩花上的军持和八辐金轮还是很清楚的。
最下面一尊造像,也是首都博物馆的藏品。与其说是供辨识佛像用,还不如说是佛像欣赏用。这一尊有两个特征表明他是弥勒菩萨:说法印和头顶的塔。但又一个特征很容易让人以为他是观自在菩萨,他左肩膀上披的象征慈悲的仁兽皮,是四臂观音或者观音化身的不空羂索的标识。不知怎么,这尊弥勒菩萨也披着。为这个,我和网友@柳叶氘交流了一次,大家都认为,另外两个特征更有说服力,就采信了弥勒菩萨的说法。读者可能会问:既然说是慈悲,怎么剥兽皮穿?得这么回答:一切佛像都是为了表达,而非观相。并没有这么一位菩萨身披血淋淋的兽皮前来说法,而是要在造像的有限空间里,安插进来一个符号。